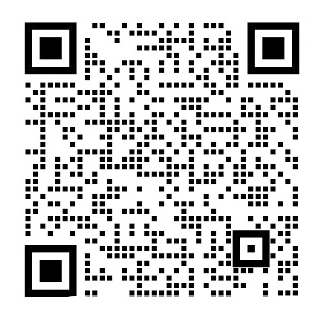青少年欺凌被害与越轨行为机制研究——基于一般压力理论毕业论文
2020-03-27 11:27:26
摘 要
本研究基于武汉市10所初中共1634份样本,在一般压力理论视角下使用SPSS 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解释了中国青少年“欺凌受害-越轨行为”机制,并探索了其中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1)欺凌受害与愤怒、抑郁情绪之间具有正向关系;(2)愤怒情绪在“欺凌受害-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则不显著;(2)欺凌受害后,女性比男性更易产生抑郁情绪,且更倾向于选择消极被动的应对策略,而男性比更倾向于选择报复反击策略
关键词:一般压力理论;性别差异;结构方程模型
Abstract
Based on 1634 samples from 10 junior high schools in Wuha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using SPSS AMOS softwa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pressure theory, and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teenagers, and explor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anger and depression;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nger on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mediator effect of de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 (2) after bullying, women were more likely to produce depression than men, and we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Choosing passive coping strategies, me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revenge strategies.
Key Words:GST;gender differences;SEM
目录
第1章 研究背景 4
第2章 文献综述 6
2.1 一般压力理论 6
2.2 欺凌受害和越轨行为关系机制 7
2.3 “欺凌受害-越轨”机制中的性别差异 8
2.4 研究假设 9
第3章 方法论 10
3.1 数据收集 10
3.2 测量 10
第4章 分析结果 12
4.1 欺凌受害和越轨行为机制 12
4.2 欺凌受害和越轨行为机制的性别差异 17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21
附录A:欺凌受害应对策略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23
第1章 研究背景
在过去数十年间,欺凌(bullying)尤其校园欺凌问题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欺凌被定义为一种长时间持续的、并对个人在心理、身体和言语遭受的攻击,并且由于欺凌者与受害者之间权力或身体力量等的不对等,而不敢或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Olweus,1994)[[1]]。欺凌的对象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其目的在于获得权力、威望或者钱财(Huang,2013)[[2]]。欺凌可以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形式,其中直接欺凌既包括推搡身体、击打某人、毁坏他人财物等直接身体欺凌,也包括辱骂、讥讽、威胁他人等直接言语欺凌;而间接欺凌则包括传播恶意谣言、社会排斥等。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传统形式的欺凌(如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等)有所减少,而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利用信息技术骚扰、威胁或针对他人的网络欺凌却出现了抬头的迹象(Hymel,2015)[[3]]。
校园欺凌是一种发生在教育环境中的欺凌现象,并非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事实上全世界都存在这类欺凌受害现象。如美国德州一项对黑人与拉美裔6至12年级儿童的研究表明12%的学生声称受到过校园欺凌,与此同时有4.5%到9.4%的学生承认参与过欺凌他人(Peskin,2006)[[4]]。Wolke等(2001)对2377名6至8岁英国儿童以及1538名德国8岁儿童的研究显示,英国和德国每周受欺凌的儿童占比分别为24%与8%。[[5]]中国香港一项针对7025名小学生的研究中有24%的受试者承认欺凌过他人(Wong等,2008)[[6]],而大陆方面,在北京、杭州、武汉、乌鲁木齐等地的9015名中学生里有25.7%在过去30天内受到过1次以上的欺凌(Cheng等,2010)。[[7]]除此之外,同属亚洲文化圈的韩国中学生中欺凌他人与欺凌受害者的占比分别为17%和14%(Kim等,2004)。[[8]]由此可见,校园欺凌与受害不仅普遍发生在不同国家,而且在小学至高中的不同教育阶段中也十分普遍。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性调查,相关数据大多是学者或机构出于研究目的选取某一地区测量得出。如张文新(2002)基于山东省和河北省的城市、县城和农村三类地区共9200余名中小学生的研究显示,有22.2%的小学生以及12.4%的初中生受到欺凌。黄亮(2017)基于中国四省市的研究表明有30.8%的学生近一年来受到其他学生的戏弄;22.6%的学生遭受过其他学生的故意忽视;而10.7%的学生受到过身体欺凌,具体形式为受到其他学生的击打或推搡以及受到威胁[[9]]。
校园欺凌伴随着攻击与反社会行为的潜在问题,被欺凌往往带来负面的社会化发展(Rodkin,2016)[[10]]。长期看来,这种负面社会化会持续至成人,进而导致过早的性行为、滥用酒精或其他药物、犯罪、辍学、失业等结果(Tharp-Taylor,2009;Farrington,2011)[[11]][[12]]。Schreck(2006)的纵向研究认为欺凌受害经历使得人们在日后的生活中选择改变生活方式,如犯罪或接触犯罪同辈等。[[13]]Hanish(2002)的追踪研究一表明早期遭遇同辈欺凌的经历与越轨犯罪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14]]
我国当前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因、反欺凌对策及法制法规上,而对青少年欺凌受害-越轨行为关系的研究非常少。与之相对的是,国外对青少年欺凌受害-越轨/犯罪关系的研究非常普遍。Agnew(1992;2001)提出的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15]][[16]]将被害经历视作一种压力源,是解释欺凌受害-越轨/犯罪机制关系机制的较好视角。本文基于武汉1634名初中生的实证数据,以一般压力理论为分析视角,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越轨行为的关系机制,二是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越轨行为机制中的性别差异。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一般压力理论
Robert Agnew的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后一律简称GST)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由Merton的失范/压力理论发展而来[[17]]。Merton(1938)理论的核心是 “结构性紧张”,即社会成功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当人们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这些社会文化所推崇的目标,就可能转而尝试各种非法手段,于是越轨行为产生了。Cohen(1955)在Merton的基础上提出了犯罪亚文化理论(delinquent subculture theory),认为社会底层青少年的犯罪本质上是对社会中上阶层价值观的一种反抗,其手段就是建立一套新的亚文化价值体系[[18]]。Cloward和Ohlin(1960)借鉴了Cohen与Merton的理论,将犯罪亚文化理论发展为差别机会理论(different opportunity theory),将亚文化细化为犯罪亚文化、冲突亚文化以及逃避亚文化,认为青少年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达到社会目标,又受到所处环境中合法/非法机会的分布不均而导致挫折,以至于用越轨行为加以回应[[19]]。
综上所述,传统的压力理论(1)主要以制度不平衡解释越轨或者犯罪,忽略了其他的社会因素与个人特质;(2)无法解释为何一部分社会低阶层的人不犯罪以及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犯罪行为,这也是其理论局限所在。
相较于传统的压力理论,一般压力理论在解释越轨和犯罪上更有解释力。Agnew(1992)认为压力是导致越轨犯罪的主要因素,而犯罪与越轨行为则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方式。不同种类的压力(strain)会引起各种负面情绪,如愤怒、抑郁、焦虑、怨恨等,而当负面情绪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得以解决时,人们就可能选择越轨或犯罪的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比如报复欺凌者,或者使用毒品[[20]]。具体来说,一般压力理论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GST拓展了压力(strain)的概念,将所有令人沮丧的条件或事件都界定为压力,并将其归为三类。第一,现有或预期无法实现积极目标,如在学校中未达到理想成绩等;第二,现有或预期正面刺激的消失,如与恋人分手、父母病逝等;第三,现有或预期的负面刺激,如被家人虐待、被欺凌等。GST认为容易导致越轨的压力有四种特征:(1)压力巨大;(2)压力被视为不合理;(3)社会控制水平较低;(4)易于通过越轨方式解决或被鼓励使用越轨方式解决问题 (Agnew,2006)。
其次,压力可能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的负面情绪,比如抑郁、恐惧、焦虑、愤怒等,不同的情绪可能会导致不同越轨行为。如愤怒情绪会使人拒绝接受挫折,将其归因于别人,因此会导致个体受伤感增加,使人渴望复仇,强化个体行动力,削弱其抑制力,进而导致外向型越轨(outer-directed delinquency)或犯罪。内向型负面情绪如沮丧、绝望和抑郁可能会导致内向型越轨(inner-directed delinquency),例如药物滥用、酗酒等(Agnew,1990;Agnew,1992)[[21]]。
最后,压力并不必然导致越轨,而应对压力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认知应对,如假装不在乎所受伤害、放大压力积极面/缩小压力消极面等。此种应对策略通过改变个体对压力的主观认识来自我调适,使个体接受挫折,降低了越轨的可能性;二是行为应对,主要表现有两种:最大化正面结果/最小化负面结果以及复仇行为。行为应对的形式可能表现为传统行为,也可能表现为越轨行为。例如学生受到欺凌后希望逃离有压力的学校环境,可能采取“转校”的方式(传统行为),也可能采取“逃课”的方式(越轨行为)。与最大化正面结果/最小化负面结果相比,复仇行为更有可能导致越轨;(3)情绪应对,即个体为了减轻负面情绪的痛苦而采取的直接作用于情绪的策略,如滥用药物缓解生活压力等。当前两种应对策略不可行或不成功时,个体更可能采取情绪应对策略。需要说明的是,此种应对策略仅仅是“缓解”压力,却并没有在认知上“理解”,或在行动上“改变”压力,因而有导致内向型越轨的可能。
2.2 欺凌受害和越轨行为关系机制
同众多受害经历一样,欺凌受害在GST中被视作一种可能导致越轨行为的压力源。众多研究证实了欺凌受害与越轨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如Barker(2008)对13至16周岁青少年的研究证明受到同辈欺凌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越轨犯罪。[[22]] Sullivan(2006)对276名以美国黑人为主的八年级城市公立学校学生的研究也表明受到身体欺凌与酗酒以及越轨犯罪行为显著相关。[[23]]此外,关于欺凌受害与越轨犯罪的纵向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欺凌受害经历与越轨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McGee等(2011)认为儿时的欺凌受害经历会导致成年后的侵略性问题[[24]];Gibb等(2011)跟踪研究1265名新西兰青年从16岁至30岁,结果表明欺凌受害经历与成年后的越轨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5]]。Schreck(2006)对1500名6至7年级学生持续5年的研究也认为欺凌受害经历使得人们在日后的生活中选择改变生活方式,如犯罪或接触犯罪同辈等。而在此过程中起到根本作用的是“自我控制水平”,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人比自我控制水平较高的人更易在欺凌受害后转而越轨犯罪。[[2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欺凌受害经历与越轨犯罪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如Bender(2011)对63名男性进行了长达10年的纵向研究,虽然结果表明欺凌受害与越轨犯罪之间则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也承认这可能与研究样本选择较为单一有关。[[27]] Bijleveld等(2011)的研究虽然发现欺凌受害与性犯罪(再犯)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欺凌被害和其他越轨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并不显著。[[28]]
欺凌受害-越轨行为机制的研究中另一个重点是负面情绪的中介效应,研究者大多将负面情绪锁定在愤怒、抑郁等情绪上,尤其是愤怒。然而,对于愤怒的中介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支持Agnew理论中负面情绪影响越轨行为的结论,如Sigfusdottir的一系列研究(2004;2008;2009)表明欺凌他人与欺凌受害都通过愤怒情绪的中介效应导致了偷窃、破坏、暴力等越轨行为;而与此同时,抑郁情绪对越轨行为的影响则并不显著。[[29]][[30]][[31]]韩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纵向研究(Moon,2009)检验了GST中“压力-负面情绪-越轨行为”模型,支持了Agnew的主张。[[32]]但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观点,如Walters(2017)基于572名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在欺凌受害和越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认知冲动(cognitive impulsivity)而不是愤怒情绪,这表明在分析“欺凌受害-越轨犯罪”机制时犯罪生活方式理论中的变量可能具有重要意义。[[33]]另外,Moon的后续研究(2012)则认为愤怒并不是一种中介变量。[[34]]总之,对于愤怒情绪在欺凌受害-越轨行为机制中的检验较多,但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而对于抑郁情绪的检验则相对不足。
面对欺凌,受害者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而不同的应对策略对欺凌能否促成越轨行为有重要影响,不恰当的应对策略会显著提高越轨犯罪的可能性[[35]]。当前研究一般将应对策略分为解决问题策略、攻击性策略以及回避型策略三种。其中解决问题策略与欺凌受害显著相关,而攻击性策略则放大了欺凌受害对越轨犯罪的影响(Rosario等,2003),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欺凌受害(Mahady等,2000)。[[36]]而回避型应对策略(回避、报复反击、内化)一方面抑制了欺凌受害对越轨犯罪的正向影响(Rosario等,2003),另一方面又与越轨犯罪显著相关(Dempsey,2002)。[[37]][[38]]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多为探索性研究而缺乏验证性研究,另一方面大多研究仅探索单一种类应对策略,而少有探索多种策略影响的综合研究。
2.3 “欺凌受害-越轨”机制中的性别差异
在“欺凌受害-越轨”机制中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不同性别的个体在面对相似欺凌被害经历时,可能产生不同的负面情绪以及使用不同的应对策略,而这些对其越轨行为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面临非民族文化、种族和宗教欺凌时,女性比男性更易产生抑郁情绪(Pan,2013)。[[39]]基于中国城乡青少年数据的一系列研究,Bao等(2007;2014)的研究发现,女生在被欺凌后更倾向于寻求多个领域(如家庭、朋友、同事等)的支持资源,而男生则更易受到越轨犯罪同辈的影响。[[40]][[41]]Cullen等(2008)的研究同样验证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如欺凌受害经历会显著导致中学男生滥用药物与酗酒,女生则不会,但这种差异的原因还尚未得到清楚的解释。[[42]]
性别差异在青少年应对策略的选择中也有着显著影响,如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面临压力时更倾向于选择寻求社会支持的应对策略(Belle, 1987)。[[43]]另外,同样的应对策略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比如DiClemente(2017)的研究表明,对于男孩而言,消极回避策略增加了越轨犯罪的可能;而对于女孩来说,消极回避策略则抑制了欺凌受害到越轨犯罪的正向关系。[[44]]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在男女应对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少有关于同种应对策略对男女影响差异的研究。
2.4 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讨两个方面,一是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越轨行为机制,包括负面情绪的中介效应以及不同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二是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越轨行为机制中的性别差异。基于以上文献,提出6个研究假设:
假设1:青少年欺凌受害与越轨行为呈正相关。
假设2:“抑郁情绪”在“欺凌受害——越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3:“愤怒情绪”在“欺凌受害——越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4:应对策略“积极协调”抑制了“欺凌受害”到“越轨”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5:应对策略“消极被动”抑制了“欺凌受害”到“越轨”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6:应对策略“报复反击”抑制了“欺凌受害”到“越轨”之间的正向关系
第3章 方法论
3.1 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于2017年10月至11月在武汉市收集。武汉市是中国中部湖北省的省会,2016年有1076.62万常住人口,共有7个中心城区和6个邻近郊区(武汉市统计局,2017)。[[45]]本研究共选取3个中心城区以及2个郊区,在这抽取的五个区中随机抽取两所中学,共有10所学校参加了研究。每个学校会从7年级和8年级随机选取1个或2个班,从9年级随机选取1个班。所有被选班级的学生都被要求在一堂课(45分钟)的时间内填写一份匿名的自填问卷。在填写问卷时,班级内会有一位研究助理在现场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填写问卷前告知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本研究为自愿参与,信息会严格保密。
共发放问卷1651份,回收问卷1646份。排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34份,问卷回收率为98.97%。本研究样本中共有男性855人,有效占比52.9%;女性761人,有效占比47.1%;样本平均年龄为13.06岁(SD = 0.91694),初一学生占比为31.02%,初二学生占比为39.72%,初三学生占比为29.26%;绝大多数母亲(46.01%)以及绝大多数父亲(46.6%)的教育程度为初中。
3.2 测量
除控制变量外,本研究中所有的变量的测量都由复数题项加总取平均值得到,编码后每个变量的得分越高,其所表示的状态程度越深。
课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